公众号:九州妖怪百集
作者:且先森
七月中旬,杭州城外,西子湖边。
一位身材高大的青年男子,书生模样打扮,正沿着岸闲庭散步。
他身边跟着个小厮,肩上扛着包裹,手里提着行李,气喘吁吁。
“我说蔡三哥…”
青年男子骤地停下脚步,扭头瞪了小厮一眼。
“好好好,蔡公子、蔡少爷,我说赶了一天的路,咱能不能先找个地方住下来?虽说蔡大娘平时多照顾咱,可人也得歇歇是不是?”
……
小厮絮絮叨叨地说着,姓蔡的书生却再不理会,只是暗地里捏了捏袖筒里的碎银子,有点发愁。
眼见日已过午,两个人的肚子都饿得“咕咕”叫。
到了车来人往的北关门外,蔡书生左瞅右瞅,领着小厮进了家馆子,要了两碗片儿川,加大份油渣儿,看着隔壁桌上的东坡肉、西湖醋鱼、龙井虾仁、红烧卷鸡、干炸响铃、咸笃鲜,稀里哗啦地吃了个半饱。
从饭馆出来,俩人一路走一路问,没有一家客栈有空房。
这也难怪,丁卯年秋闱将近,赶赴各省贡院的秀才们络绎不绝,客栈不爆满才怪。
“柴房倒是有一间”,客栈的掌柜犹豫了下,又道:“堆了些干茅草,不过有个道人同住…”
蔡书生皱皱眉头,心道:这不年不节的,不好好地侍奉三清,跑到杭州城里干什么?
小厮搓着手正要答话,看看蔡书生的表情,顿时泄气三分。
“都怪你,一路走一路停,说是看风景…”
从客栈出来,两人困乏不堪,坐在路边歇息,小厮仍兀自说个不停,蔡书生也不理会他,权当自言自语。
街上人来人往,挑担的、卖货的、吆喝的,络绎不绝,蔡书生左右张望个不停,看到某处,忽然眼睛一亮。
“你且在这里看管行李,我去去就回。”没头没脑地叮嘱了这么一句,不等小厮问话,蔡书生起身兴冲冲地朝着对面去了。
眼前是一个独门小院,门前地面杂草丛生,看样子许久没人住了。
墙上贴了张破破烂烂的纸,歪歪斜斜地写了几个大字:本屋贱卖。
靠近点看,纸下面还有一层,是“运河口,西湖边,距离贡院仅4里地,只租不售,一口价,租金不议”云云。
不远处有个房牙子,佝偻个腰,抄着手蹲在地上,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看到一个人一溜小跑冲向自己,房牙子吓一跳:光天化日之下还有劫色的?
他跳起来,后退一步,气沉膀胱,摆出二字钳阳马。
蔡书生在离他三尺处刹住身子,拱拱手,刚要张嘴,房牙子抢先道:
“卖!”
欸?这……蔡书生呆了呆,正待问问心中最为紧要的问题,房牙子又道:
“4两!”
蔡书生有点犹豫,踌躇再三,颇想问问能不能再让点零头。房牙子瞅他一眼,收了架势,冷冷道:
“3两!契税3钱!当日画押,概不反悔!”
蔡书生大喜过望,把话咽到嗓子里,慷慨道:“那就来吧!”食指伸到嘴边,眼睛一闭,就要狠狠咬破。
房牙子一脸怪异,道:
“你脑西靠册的啊?又不是卖身!”
说罢从怀里摸索出一盒朱砂印泥,又掏出两张契据来念道:
“浙江杭州府北关门外茶铺王四平,今将原买省城住宅一所共计瓦屋一间,出卖与绍兴府蔡炳侯名下为业,实授价银三两,银钱两讫,恐后无凭,立此卖契,文约为照。”
一口气念完后,房牙子将契据伸到蔡书生脸前,道:“画押罢!”
“慢着!”
蔡书生猛然想起什么,按住房牙子的手,问道:
“族亲次邻都已问妥?”
房牙子不耐烦地甩开蔡书生,指头捣着契据哗啦作响,道:
“上面都写明了,官印手印一应齐全!”
蔡书生忙不迭抢过印泥,两下按完,拿过契约,粗晃一眼,叠好放进怀里,拱手道:“有劳啦!”
房牙子看他一眼,道:“不送!”转身便走。
“蔡心,蔡心!”
话说小厮正蹲在路边打盹儿,忽听得有人叫自己,睁眼一瞧,原来是蔡书生在街对面大呼小叫,打着手势要自己过去。
蔡心翻翻白眼儿,吭吭哧哧,一步一挪,把行李和自己都搬了过去。
蔡书生兴高采烈地跟蔡心讲述了自己如何“低价”买来小院瓦屋一间。
蔡心耐着性子听完,转头看看院门上生锈的大铁锁,一脸懵逼地问蔡书生:“钥匙呢?”
蔡书生:“……”
离小院落不远处的拐角,一个贼眉鼠眼的小老头,正在跟房牙子嚷着什么。
房牙子无话可说,转身回来,刚走了几步,不料和人撞了个满怀。
房牙子一抬眼,心道:找的就是你呀!
“银子呢?!”
来人定睛一看,嚯!
“钥匙呢?!”
房牙子和蔡书生大眼瞪小眼,同时诘问对方。
瞬间,两人脸上又迅速换成了谄媚/客套的笑容:
“哈哈哈哈哈!”
“这真是误会,哈哈!”
“对呀对呀,哈哈!”
真正的“银钥两讫”之后,俩人站在原地,认真想了半天,终于一同点点头,道:
“告辞!”
“不送!”
蔡书生和小厮蔡心,打开院门,一地荒草,绿油油的。
把行李靠到墙边,蔡书生反应迅速,马上道:“初来乍到,我去和街坊四邻打个招呼,好有个照应,你且在此打扫院落。”
蔡心埋怨道:“怎么就忘了把家里的牛牵过来!”
蔡书生哼着小曲,踱步到一旁的豆腐店,正要开口,豆腐店“哐当”一声,扣上了门板,连个人影儿都没见。
往前走两步,是一家油铺,蔡书生到店门口,作了一揖,道:“店家,我是新搬来的,不才姓蔡,还请以后多多…”
话还没说完,里面正在打油的中年妇女,瞅他一眼,向着老板喊一声道:“明日来取!”然后油也不要了,转身慌慌张张就跑远了。
蔡书生一头雾水,想要问问油铺老板,“哐当”、“哗啦”两下,对方连门闩都给插上了。
真是活见鬼了!难道我额头上长角了不成?
蔡书生一面愤愤地嘟囔着,一面伸出手挠了挠头。
索性,回去帮蔡心收拾院子好了!
转身往回走,却看见一个干瘦老头,在站在院门口,探头探脑地往里瞧。
蔡书生踮起脚尖,悄悄走到老头后面,拍了拍对方肩膀,后退一步,张开双臂,道:
“大爷!”
老头扭过脸,瞅瞅蔡书生大鹏展翅一般的姿势,心道:这孩子可别是个智障吧!
蔡书生热情洋溢地问道:
“大爷你别走,大爷你怎么称呼,大爷你有什么事?”
老头转身,道:
“哦,小伙子,是你买了这院子?”
蔡书生彬彬有礼道:
“正是,大爷有何见教?”
老头往周围看了看,压低了声音,神秘兮兮道:
“见教不敢当,小伙子,我可告诉你啊,这院子可住不得人啊!”
“怎么地呢?”蔡书生也压低了声音道。
“这屋里头啊——闹鬼!”老头凑到蔡书生耳边。
“啊——
蔡心正在院子里侧耳细听,听到“闹鬼”,吓得笤帚一扔,哇哇叫着从里面冲了出来,一把抱住蔡书生,带着哭腔道:“三哥,我怕!”
蔡书生推开蔡心,面色严肃,郑重其事地问道:
“男鬼女鬼?”
“什么?”小老头眨巴眨巴眼睛,不解道:
“吊死鬼呀!听说…死了好几个人!”
“哦…”蔡书生若有所思,默默地从袖筒里摸出一文钱,塞到老头手里,道:
“芳龄几何?”
老头飞快地把铜钱塞到怀里,悻悻道:
“女鬼。”
蔡书生满意地冲小老头拱拱手道:
“老人家贵姓?府上是?改日一定登门拜访。”
小老头笑笑,得意道:“不敢当,小老儿姓王,名四平,家在城南。”
刚说完,看见蔡书生已经拉着那小厮走远了,还能隐约听到他兴奋的声音道:
“……怎么样蔡心?今夜陪小爷我夜访吊死鬼如何?”
老头:“……”
蔡心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道:
“三哥,我就不打扰你温书了,你给我十文钱,我去住店好了。”
蔡书生啐道:“没志气!”遂从袖筒里数出二十文,大方地递给蔡心,道:
“省着点花!”
蔡心接过钱,头也不回。
天很快黑了,蔡书生没处去,就在院子附近踅摸。
远处的西子湖畔,结队的妇女们正在放湖灯,把折成荷花状的彩纸中间,点上蜡烛,轻轻推向湖中央,寄托哀思。
道路两侧,也有人摆上了一排排蜡烛,巷子里的小孩子,提着荷叶灯,蹦蹦跳跳地唱着:荷叶灯,荷叶灯,今日点了明日扔…
蔡书生看得有趣,不由得走远了些,见很多院门开着,庭院中央摆着莲蓬、藕、老菱、盐水毛豆等各色时鲜,一家人团团围坐。
家家喧闹,唯独自己形单影只,蔡书生心生羡慕,想起小时候,常常和小伙伴挤在人群里,争看目连戏,禁不住微笑起来。
逛了许久,蔡书生无聊起来,到路边摊贩处,买了些蜡烛等一应生活用具,便径自回去了。
院子里静悄悄的,半尺高的青草,映着天上的一轮缺月。
蔡书生点好烛火,看看屋里,到处都是灰尘,墙角还结着几张蜘蛛网,大皱眉头。
扒开行李,他找出块破布来,往床上、桌子上拍打,腾起一阵灰尘,呛了个灰头土脸。
“咳咳…咳,咳咳咳…”
蔡书生冲出房门,拼命地咳了一阵子。
无奈,他只好到灶房里看了看,找了个破木桶,出门到附近提了半桶水,耐着性子把桌子、凳子、床板擦拭了一遍。
满意地看了看自己的劳动成果,蔡书生从行李里掏出本《孟子》,摊开放在桌上,看了一阵子,打了几个哈欠,就起身又去扒出一册《搜神记》,摊开放在《孟子》上,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
大约子夜时分,蔡书生实在是困得不得了,趴桌子上打起盹来。
迷迷糊糊地,他看见窗外有人影,摇晃着什么东西。
哦?
蔡书生一个激灵,醒了。
他倒是也不着急,站起来搓了搓脸,伸个懒腰——哎,舒坦!然后——又坐下了。
“嗯…哼!”蔡书生正襟危坐,清了清嗓子,朗声道:“蔡某人恭候多时了,阁下请进寒舍详聊!”
……
“噼啪”一声,烛台上的蜡烛炸开了一个烛花,蔡书生吓得一哆嗦。
……
皱了皱眉头,蔡书生高声道:“请足下进来吧!”
……
许是在这方凳上坐得太久了,蔡书生挪了挪屁股,心道:难道是自己太过困乏,看花眼了?
再看看窗户上,是有个人影儿。
蔡书生双手合拢,围在嘴边做成喇叭,运足中气,道:“请——进——来——吧——!”
……
“人儿登!你脑西靠册的啊?生更半夜壕丧哇?!”
大概是隔壁实在听不下去,嗷嗷地骂了一嗓子。
蔡书生一愣,腾地站起来,抬脚踏在凳子上,一捋袖子,正准备开怼——
窗外紧接着“当啷”一声,隔壁又不知道把什么东西砸到院子里了。
咦——哈!老子真当是话语阿没的!
蔡书生火气上头,两步上去,拽开房门,要冲到院落里,抄起点儿啥玩意儿,扔他娘的回去!
……
他没料到脚下还有门槛。
哎哎哎哎…哎——!
那一刻,蔡书生能感觉到耳边有风经过。
不过,没有想象中的鼻青脸肿、眼冒金星,他像是撞到了花丛中一般,软绵绵的,摔了个温香满怀。
“呜呜呜呜呜——”
蔡书生正晕头巴脑地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耳边响起了女人幽幽的哭声。
“我——去!”
一低头,自己居然趴在一个女子身上!
可能是周围太黑,慌忙间也看不清楚这女子的面容,蔡书生慌忙爬起来,后退几步,拍拍身上的土,深深作揖道:“小生这厢有礼了!”
对方也不答话,只是低头抽抽噎噎地小声哭泣。
“嘤嘤嘤…妆…花了…呜呜…发…髻歪了…凝聚散了…呜呜呜…”
“那个…你…这个…”蔡书生觉得尴尬极了。
亚圣云:男女授受不亲。
自己不光是把“人”给撞倒了,还跟人家“亲密接触”了一番,这…唉,成何体统!
不过,对面女子的声音,还蛮好听呢。
小时候上树抓鸟下河捞鱼,蔡书生没少听他娘哭教,对女人哭甚是头疼。
他正抓耳挠腮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忽然灵机一动,问道:“敢问这位姑娘,刚才可是你在窗外招手?”
“…嗯!”
“那小生在屋里呼喊许久,姑娘你为何不进门呐?”
……
蔡书生只觉得眼前一闪,那女子像是枯叶一般“飘到”自己面前,伸手就是一耳光,道:
“你有本事喊我,怎么不给老娘开门啊?!”
蔡书生一愣,脸上没有熟悉的火辣辣感觉,却仿佛有一阵微风从脸颊旁刮过,只觉得凉丝丝的。
那女子动完手,倒也不再哭了,径直往房间里走去。
从背后看,女子颈缠红帛,披头撒发,走起路来娉娉婷婷,身姿优美,好像弱风扶柳,足不沾地,煞是好看。
蔡书生咽咽口水,也跟着进屋了。
女子进屋站定,向着蔡书生叩了个万福,蔡书生这时才睹到她的模样:
一袭月白碾绢纱湘裙,纤纤细腰,不足盈盈一握,泼墨般的长发落在瘦削的肩上,发间插着一朵洗手花,瓜子脸,细峨眉,一汪秋水般的含情双目,柔情欲望,俊俏鼻梁下,嘴角边有一粒俏媚黑痣,两片紫青色的薄唇,微微含笑,露出一颗好看的小虎牙,只是脸色格外的苍白。
末伏已过,江南的暑气还未散尽,然而这女子往屋里一站,蔡书生莫名的觉着一阵寒意,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女子也不说话,伸手露出雪一般的皓白手腕,兀自解下颈上红帛,往上一抛,红帛在空中伸展开来,缓缓飘落。
她跺跺脚,嘟起嘴,俯身捡起红帛,侧身用力将之挥出,然而,红帛飞到半空…又掉下来了。
……
这女子看来性子较为倔强,几番下来,还是把那红帛抛个不停,蔡书生看得直打哈欠。
他从行李里翻出一方砚台来,接住飘落的红帛,用捆蟹的手法把砚台牢牢固定,瞅准房顶横梁,稍稍用力一扔,红帛老老实实飞上半空,绕过房梁,垂了下来。
女子抿嘴一笑,冲蔡书生又福了一礼,走上前去,将方凳横放,提起裙摆,站上去,解下砚台,把红帛挽了个结,伸头套了进去,踢开脚下凳子,竟是自缢一般,吊在了半空中。
蔡书生把凳子放好,微微抬头,向对面上吊的姑娘拱了拱手,道:
“小生姓蔡,名炳候,这厢有礼了。”
女子:
“……”
“姑娘贵姓?”
“……”
“小生到此赶赴乡试,姑娘是杭州府人吗?”
“……”
“姑娘你有兄弟姐妹吗?”
“……”
“姑娘,你我一上一下,说话尤为不便啊!”
那女子脸色转为绯红,她在空中挣扎了一下,双手抓住红帛做的绳套,用力撑了撑,怒道:
“少年,你是不是傻?我这样怎么开口说话?”
蔡书生搔搔头,心道:也是啊。于是,又把方凳横放,挪到女子脚下,不解道:
“姑娘,你就准备这么挂着跟小生说话吗?”
女子脚下有了东西,蹙眉想了想,从凳子上跳下来,在袖子里摸出另一条红帛来,照着蔡书生的法子,又做了一个上吊专用脖套,跟蔡书生招招手,示意他也挂上来。
蔡书生依言上前,把脖子往“脖套”上一放——原来这女子身材娇小,个头只到蔡书生胸前,她需要踩着横放的凳子,才能够“挂”着的位置,却正好和蔡书生的下巴平齐。
如此一来,两人皆开口无虞,蔡书生期期艾艾道:
“还不知姑娘芳名?”
女子现出迷茫的神色,自语道:
“我叫什么?可是我忘记了…”
不过她很快高兴过来,向蔡书生道:
“不过我给自己起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小曼。”
说罢一挑细眉,问道:
“你觉得好听吗?”
蔡书生顾不上想她如何就忘了自己的名字,忙不迭点头道:
“好听好听!…小曼是杭州府人氏吗?”
小曼道:
“不知道哎,你这个人怎么问题这么多?”
蔡书生有些意外,道:
“别人问题不多吗?”
小曼看上去有点郁闷,她皱眉道:
“是啊,一见到我的模样,脸都变成酱色,哭爹喊娘的,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蔡书生心想这些人真的是不解风情,随口问道:
“你…什么模样啊?”
小曼兴奋道:
“对哈对哈,还没给你看过呢!”
说罢,小曼把头发都拨到头前,遮住小脸,问道:
“你准备好了吗?能不能帮我喊个一二三?”
蔡书生不明所以,道:
“好,一…二…三!”
小曼本来和蔡书生相隔不过两尺,就在他话音刚落的一霎那,蔡书生忽然觉得,小曼的头,一下子伸到了自己面前!
只见小曼猛得把头发分开,瞪圆眼睛,吐出小舌头,双手举起,葱指微拢,一脸严肃,作势欲扑!
蔡书生与小曼的脸相距不过分毫,只觉得她呵气如兰,不由得面热心跳。
小曼兴高采烈地问道:
“怎么样,厉不厉害?你害不害怕?是不是快要吓死了?”
蔡书生哭笑不得,看小曼一脸期待,只好假意道:
“嗯,我好害怕。”
假装平静地向后移了移身子,蔡书生问道:
“小曼,你来杭州府多久了?有家人在这边吗?”
小曼歪头想了想,漫不经心地道:
“我没数过哎,只知道娘亲带我逃荒来杭州那年,闯王正闹京城呢!”
“闯王…闯王?!”
蔡书生心头顿时一惊!
现今是乾隆爷登基二十一年,从前朝到现在,已经是…
再看小曼身上衣裙,这才意识到,她分明不是本朝人士!
这个女鬼,竟然已在世间飘荡了一百多年了。
“那你怎么没有投胎转世呢?”蔡书生小心翼翼地问道。
“什么是投胎转世啊?”小曼眨巴眨巴大眼睛,满脸都是我不懂你快来教教我的表情。
“这个…”
蔡书生一时语塞,冥思苦想了半天,眼睛一亮道:
“那个…你…你死的时候,有木有一个白衣人和一个黑衣人,来把你带走?”
“带走?去哪里啊?黑衣人和白衣人?他们是谁呀?”小曼依然不明所以。
蔡书生花了一个时辰,一五一十地把自童年听到成人的,什么“黑白无常、黄泉路、奈何桥、孟婆汤”之类的故事,统统讲了一遍。
小曼倒是听得津津有味,不住地要他再多讲一点。
蔡书生说得口干舌燥,头都大了——
我特么在跟一个鬼解释阴曹地府的事儿吗?
“好吧”,蔡书生最终决定放弃那些神神道道的问题。
“这一百多年了,小曼你都在做什么呢?”
“唉”,小曼叹口气,道:
“白天我就只能睡觉了,晚上才可以出来吓吓人…”
“为什么白天只能睡觉?”蔡书生好奇道。
“我也不懂啊,只要太阳出来,我就没办法凝聚身体咯~而且如果触碰到的生人太多,我的身体就会慢慢消散,那种感觉好难过的!”
这一点,小曼也不是很明白的样子,说到“难过”二字,小曼脸上明显有了委屈的表情,只是犹自说个不停:
“一开始的时候,我好害怕,身体没有了,我就找不到自己了,只知道自己还在,就是找不到自己了…”
说着说着,豆大的泪珠从小曼眼睛里涌出来,顺着脸庞下滑。
“不过到晚上的时候,我就有身体了。我也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知道是这样的。”
泪珠滴下来,掉落在空气里,没有落地,就消失了。
“只是那几年,我太想和人说话了。”小曼回忆道。
“差点就彻底消散了。”
“对啦!”蔡书生好奇道:
“别人都说…吊死鬼的舌头都很长很长的,你行么…”
“啊?是嘛?你看我舌头长吗?”小曼也来了兴趣,拼命地吐舌头。
“你这哪里长啊!”蔡书生没好气地说。
想起刚才小曼刚才“吓人”的那副模样,他却心里忽然有些疑惑:为什么人们的传言里,鬼都是那么可怕的呢?
他故意板起面孔,质问道:
“小曼,你为什么要出来吓人呢?”
“啊,其实我不是要吓人,我,我就是想…想找个人说话,不过我一出来,他们就变成那样子了。”小曼小声辩解道。
“可是,听别人说,你把好几个人都吓死了!”蔡书生语气严肃。
“蛤?怎么会?”小曼连忙摆手。
“他们从来都只是晕过去了啊,我一个柔弱女子,哪有气力把一个大活人吓死啊!”小曼撇嘴道。
“不信,你看——”小曼把手伸向蔡书生的心口,直接穿了过去,仿佛她是透明的。
“嗯。”蔡书生若有所悟。
多年以后,他方才明白,原来人们的害怕,并非是鬼多可怖,而是人的心中,藏有恐惧。
“那你见过别的鬼吗?”蔡书生道。
“没有唉,从来都只有我一个。”小曼可怜兮兮道。
“对了,你娘呢?”蔡书生忽然想起,刚才小曼有提到,是她娘带她来的杭州府。
“我娘亲啊,在我之前就死了。我也没有见过她的鬼。”小曼道。
蔡书生忽然觉得难过起来,一百多年,有多少人声喧嚣,有多少离合悲欢,阴晴圆缺,却只有小曼孤零零的,往杭州城里飘飘荡荡,无常鬼差不来拿她,阴曹地府未曾收她。
她就这样,被遗弃在繁华世间。
人死后,都是这么孤独吗?
一人一鬼相对无言。
夜很短。
鸡叫了头遍,天蒙蒙亮。
“我可以抱抱你吗?”小曼道。
“好”。
两人终于不再“挂”着,一起到桌前坐下。
小曼靠着蔡书生的肩膀,依偎到他怀里。
夜凉如水,小曼的身体比水还要冷,蔡书生想抱住她,却感受不到一点依靠的重量。
低头,就能嗅到小曼的头发,蔡书生忽然看到那朵“洗手花”,心有所动。
他轻轻地把红艳的花朵取下,放在桌子上。
“蔡三哥!蔡三哥——”
院门外响起蔡心杀猪般的急促叫声。
蔡书生揉揉眼睛,发觉自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面前惟有一方叠得整整齐齐的红帛,上面静静地躺着一朵“洗手花”。
昨夜一切,宛若南柯一梦。
刚站到门口,蔡心像飞鸟投林般紧紧抱住蔡书生的大腿,带着哭腔道:
“三哥——三哥!你可吓死我了!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可怎么跟大娘交代啊!”
蔡书生被撞得一趔趄,险些坐倒。
他这才注意到,蔡心身后跟着一个道士,就看向蔡心。
蔡心急忙道:
“这是昨晚和我一起在柴房住的道长,我跟他说了这房子闹鬼,你死活不听劝,这不,我把道长请过来,给你辟辟邪……”
“谢谢你,蔡心。”蔡书生打断蔡心的话,轻轻地说。
“呃?”蔡心一愣,喃喃道:
“我说少爷,你不是真被鬼缠身了吧?”
蔡书生被气笑了,笑骂道:
“滚蛋…”
说罢,收敛笑意,转向道士,淡淡道:
“有劳道长,小生昨晚彻夜温书,此刻有些困乏了。道长请回吧,明日再请登门。”
“蔡心。”蔡书生扶起蔡心,温和道:
“你随这位道长一同回客栈,替我招待,明日准备些用物,请道长在这里做一场法事。你说得对,该辟辟邪。银子你拿着,省着点花。”
说罢,从袖筒里掏出一块碎银子,放在蔡心手里。
蔡心瞪大眼睛盯住蔡书生,仿佛要在蔡书生身上看出来个透明窟窿,直到蔡书生作势要揍他才作罢。
……
“你说说,三哥要是没有被鬼上身,怎么会对我这么有礼貌,还给我银子…”
听到蔡心一边走还一边跟道士絮絮叨叨地说着话,蔡书生无奈地笑了笑。
看着两人走远,蔡书生洗了把脸,稍作收拾,锁上院子出门。
先是买了些熟宣、香烛纸马,然后去酒肆嘱咐晚上送些素馄饨和酒菜,想了想,他又带了一束“洗手花”回来。
研好了墨,蔡书生立在桌前,沉默许久,提起手中的狼毫,饱蘸了漆黑墨汁,在纸面上开始勾勒。
这天晚上,蔡书生把画好的白描,贴到房间墙上,摆好酒菜、香烛,还有插在水瓶中的“洗手花”,坐在桌子边,慢慢地一口口吃完馄饨,又起身出门。
西湖岸边,他点燃湖灯,轻放在湖面上,看它随着微凉的凉风,打着旋儿飘向远处去了。
缺月倒映在水面上,湖边空无一人,中元节,或是盂兰盆节,都已经过去了。
夜深了,小曼并没有来。
次日,蔡心携道士按约登门,大开院门,摆好架势,一番作法。
油铺边上,有三五个闲人围看,不时议论着:
“听说这院子闹鬼好多年咯…”
“哎呀,可不是嘛,也不知道这道士作法管用吗?”
“叫我说,应该请金山寺的和尚来…”
……
日子一天天过去,秋闱逼近,蔡书生真的常常熬夜温书了。
伴着他的,是叠得整整齐齐的一方红帛。
窗台上的洗手花逐渐地枯萎了,他原本让蔡心再买些换上,但是蔡心嫌弃那是拜祭死人用的,不肯去。
索性,蔡书生从野外,掘了些种在院内向阳处。
画呢,在那天晚上,就烧掉了。
八月,蔡书生秋闱高中解元。
次年三月,蔡书生又杏榜题名;四月殿试,考中进士,吏部授任杭州府布政使。
不久,蔡方伯婚娶,夫人是同朝为官的御史女儿。
那所独门小院,他定期着蔡心去打扫,每当有政务难缠,便会去小住几日。
两年后的中元节,祭拜完祖先,一家人正在院中赏乐,怀孕已足月的蔡夫人忽然叫肚子痛,好在稳婆是早已请在家里候着的,也不显得慌乱。
折腾了两个时辰,随着一声嘹亮的婴儿啼叫,子夜时分,蔡夫人顺利生产。
堂屋里,老妈子抱着包成粽子般的孩子,到蔡大人跟前,喜滋滋道:
“恭喜老爷,夫人诞下小千金啦!老爷快来抱抱吧!”
蔡大人自是喜不自禁,接过孩子,笑吟吟地看了一眼,差点把手里的孩子扔出去。
眼前的婴儿也不哭闹,红扑扑的瓜子小脸上,一双水汪汪的眸子望住了蔡书生,小巧的鼻梁下,是两片薄薄的小嘴唇,带着浅浅的笑意,露出一颗好看的小虎牙,而微微上翘的嘴角边,正有一粒淡淡的美人痣。
不是小曼,还能是谁呢?
文章来源于互联网:-《知妖》:大胆书生与懵懂女鬼,奇异而温暖的人鬼邂逅【缢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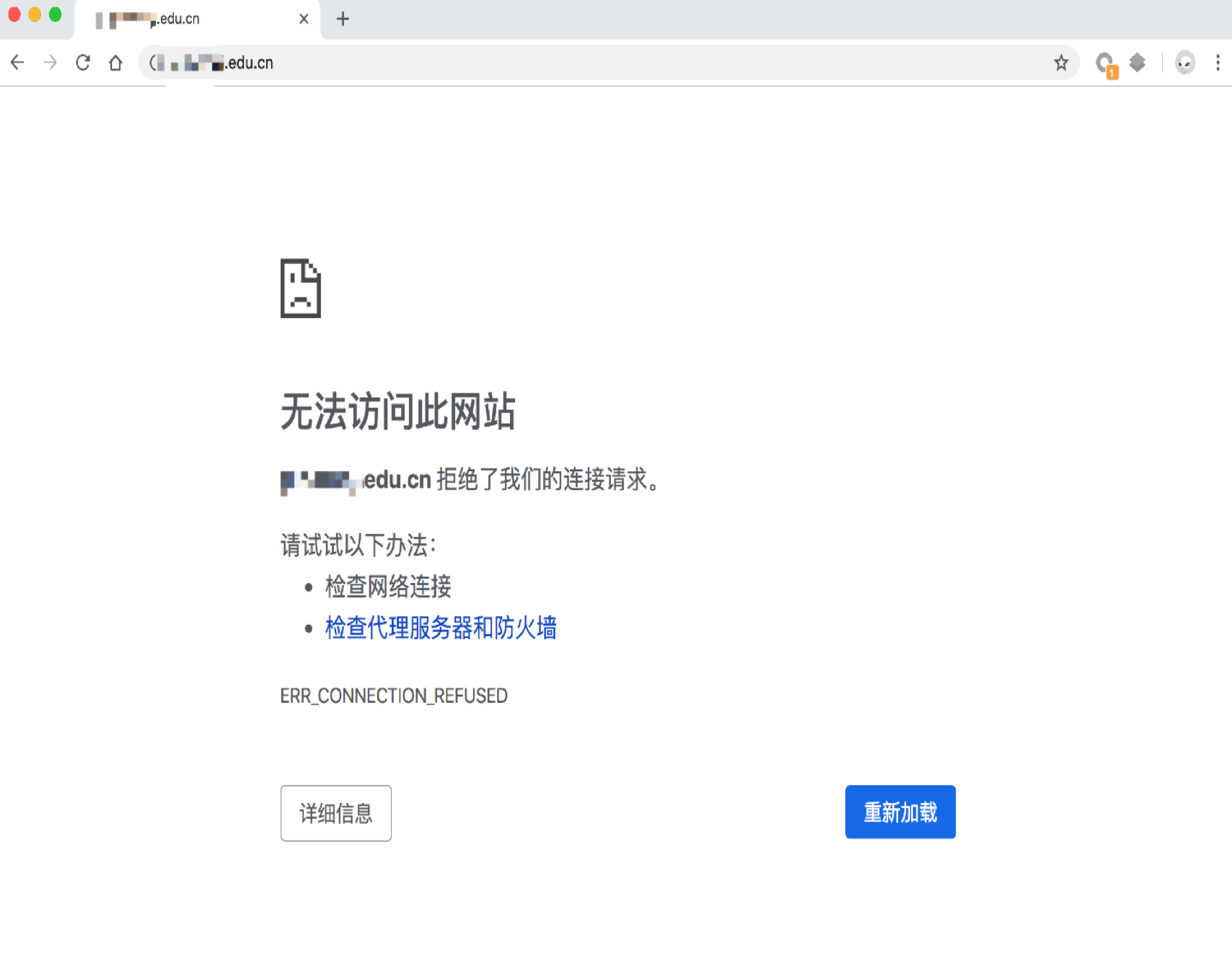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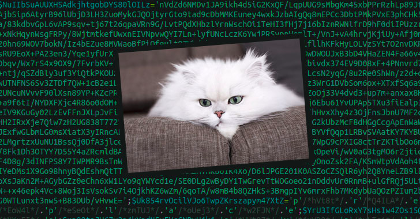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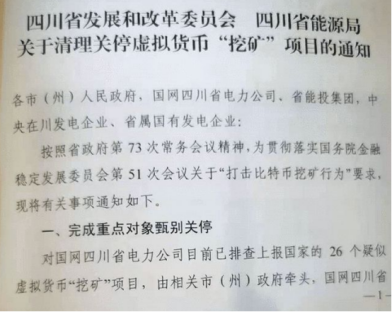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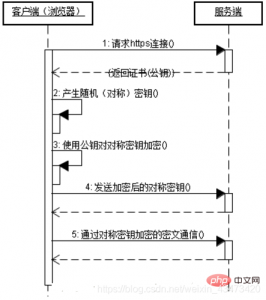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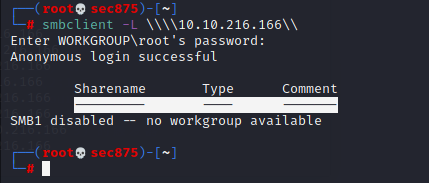



请登录后发表评论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