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知乎专栏:神州幻梦
引言
狐曾经以不同的文化面貌出现在古人的观念中。笔者尝试将其嬗变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和各个形态分别定类为「凡狐」、「灵狐」、「祥狐」、「神狐」、「瑞狐」、「狐魅」、「狐妖」、「狐神」、「狐仙」等。

魏晋之际,狐开始从「精」转化为「妖」。于是,在此后的传说记载及志怪小说中,狐便经常以人的形态面貌出现在人类活动环境中,并与人类进行交往。笔者将之定类为「狐妖」,以此和兽形的「狐精」作区分。
其等的变幻程度虽有差别,但大多都具备几乎完美的人形及明确的人类身份,甚至拥有姓名,完成了人性化甚至人格化。这些狐妖的行事方式不尽相同,按照故事的性质及其相关描述,或可以再细分为几类:「淫狐」、「狐媚」、「妖狐」、「狐妻」、「学狐」、「天狐」 、「仙狐」、「善狐」等。
作为神兽、瑞兽,比狐更耀眼的族群比比皆是,但作为妖精,无论是作祟事迹之多,还是妖异性之高,抑或是族群数量之多,狐妖都是其他妖类莫能比肩的。
明·羅貫中《三遂平妖傳》:「話說諸蟲百獸,多有變幻之事,如黑魚漢子、白螺美人、虎為僧為嫗、牛稱王、豹稱將軍、犬為主人、鹿為道士、狼為小兒,見於小說他書,不可勝數。就中惟猿猴二種,最有靈性。算來總不如狐成妖作怪,事跡多端。」
明·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天地間之物,惟狐最靈,善能變換,故名狐魅。」
明·徐昌祚《燕山叢錄》卷八:「大抵物久而為妖,有情無情皆有之,而惟青丘之獸(指狐)為多。」
狐妖身上不仅体现着一些通用的宗教观念,如「物老成精」、「象人之形」等,还体现着许多狐妖特有的宗教观念,诸如「狐妖」、「狐仙」等概括狐妖的变化和修炼的概念。
另一方面,狐妖身上还非常特殊地体现着古代中国人的伦理观、女性观等社会观念,其身上反映着的很多时候也不是文人对狐的评价,反而是对人性的认识、批判和思考。
这是狐妖相较于其他妖类最为特别的地方,也是中国狐文化的一大魅力所在。因此,在古代文学体系中,没有哪种妖物能像狐妖一般获得广大的小说家的青睐。
本系列文章将尝试对志怪故事中存在的不同狐妖形象进行概括,归纳其行为表现的特徵,并分析其形象或特徵背后的文化背景及相关的文化观念。由此让读者及笔者本身对「狐」这一文化形象有更广泛而全面的认识。
囿于篇幅,若对引录故事的原文感兴趣,请自行查阅。
六朝时期,故事中的「狐精」逐渐转化成了「狐妖」。这段时期所诞生的狐妖故事,对后世狐妖的形象造成很大影响。
其中有一类十分特殊的狐妖,这种狐妖大多都是博学而多才,喜欢谈经论道,与它们那被唤为「媚兽」、「淫兽」的同族截然不同。笔者将它们定类为「学狐。」
以下引述数则有述「学狐」的志怪故事以观之。
- 东晋·干宝《搜神记》卷一八——胡博士
此则故事中的「胡博士」,其学识足以教授诸生。
- 东晋·干宝《搜神记》卷一八——燕昭王墓斑狐
此则故事中的燕昭王墓斑狐,能化书生形。燕昭王以好士著称,此狐受其浸濡,亦为学贯百家、见识广博之士。
- 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八——胡道洽
此则故事中的「胡道洽」喜欢音乐及医术,其才学之高足以收取弟子。
- 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董仲舒之客狸
此则故事中的学狐,乃董仲舒之客狸。此客狸同样学识渊博,卓越不凡。古人以为狐、狸同类,故笔者将之归入「学狐」。
六朝记载中「学狐」形象的文化内涵
古人认为狐是「智兽」,由此便生出狐妖喜读书的传闻。
《太平御覽》引晉·伏滔《北征記》云:「皇天塢北古特陶穴,晉時有人逐狐入穴,行十餘里,得書二千卷。」
所以,这种书生化、博学化的狐妖形象亦因此诞生。总览中国妖怪传说,唯独狐的才智得到突出强调,并体现在学问之上,其他妖物莫能相比。
如果说狐妖的淫媚化所反映的是古人对狐的恶意,那么狐妖的博学化所反映的,该是六朝学士对狐的好感,对其智慧的赞美。
这种诞生在六朝时期的学狐形象,某程度上亦反映了两晋南北朝社会崇尚知识,以博学为荣的文化心态。
南梁·陶弘景《南史·隱逸傳下》云:「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
或可推而广之,以此窥探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们的共同性格。
说不定学狐就是士人用以自我投射到志怪小说中而创造的形象角色,这一点从学狐都是雄狐,好清谈论道的特征中可以窥知一二。所以当士人作者或读者对故事中的学狐萌生欣赏、惋惜之情时,这种情感的宣泄对象说不定是被学狐映射着的他们本身。
狐妖表现出儒雅、才学出众的特质,与所谓「淫兽」、「媚兽」的性质大相径庭。这种新的狐妖形象在后世狐妖故事中亦会反复出现。
唐代「学狐」的博学化现象
狐妖的博学化现象在唐代进一步加强。
唐代的学狐与六朝时期的一样,无不是雄狐,但其嗜读好学的方向与此前的学狐相比却略有不同,体现在杂艺方面的情况渐多。
- 北宋《太平广记》卷四四八引唐《广异记》之《李参军》
李参军所遇到的「读《汉书》之老人」便是狐妖,当属学狐一类,但最后被杀了。
- 同上书卷四四九引唐《广异记》之《李元恭》
崔氏所遇之「胡郎」,博学多才,有名言曰「人生不可不学」,又引三人(狐)先后为崔氏传授经学、书法和音乐,但最后都被杀了。
- 同上书卷四五一引唐《广异记》之《崔昌》
崔昌所遇之「小儿」本为狐,仰慕崔昌的学问。
- 同上书卷四五一引唐《广异记》之《孙甑生》
唐道士孫甑生本以養鷹為業,後因放鷹,入一窟,見狐數十枚讀書。有一老狐當中坐,迭以傳授。……
孙甑生所遇的窟中群狐,正在读书,亦是「学狐」一类。此处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那便是「狐书」。
- 同上书卷五四引唐《宣室志》之《尹瑗》
此则故事中的「朱生」同样是因倾慕尹瑗学问而来,亦属学狐,最后也被杀了。
——
由上引数例可见,「学狐形象」于唐代依然存在,并得到了发展。
然而,唐朝狐妖观念中还有一个与道教影响密切相关的有趣变化,那就是狐妖「好学嗜读」的特征多体现在法术方面,而不再是学问相关。
唐代狐妖的的博学化及法术化现象——兼谈「狐书」
六朝狐妖有好学之特征,故而多有学狐。
晋·伏滔《北征记》说狐穴中得书二千卷。这是狐书之始,狐读而学之,才有了胡博士之类的学狐、儒狐。
六朝时期「学狐」形象中的博学元素,在唐代扩散成为狐妖整体的特质,兼且当时存在狐妖法术化的现象,所以狐妖所看的书的内容亦从人间经史百家变成道法之术。
《广异记·李氏》中,大狐媚惑少女,「以药颗如菩提子大六七枚,掷女饭碗中」。
这显然是媚药,而小狐因与大狐争风吃醋,先后亦用药、桃枝和符禁治大狐。
同书《韦明府》中的崔狐教给其丈母烧鹊巢、持鹊头的退狐法术。
又《杨氏女》中大胡郎也通悬鹊头辟邪之术。
《宣室志·林景玄》中,老狐可以自知死日,并用死鹊禳灾。
这种学问法术化的情况明显与唐代盛行的「狐神信仰」和「天狐崇拜」密切相关,因为在唐代的「狐妖」、「狐神」和「天狐」的相关故事中,往往都有它们精于法术,善卜算的表现。
一如学狐形象中的「博学多才」特征,「精于法术」和「善卜休咎」在后世成为了狐妖一族共同拥有的特征。凡是狐妖,其故事中大多都有针对这方面的描写。
例如北宋·刘斧《青琐高议》后集卷三《小莲记》中的狐女「小莲」。
在其故事中,故事人物李郎中生病,小莲说「公无求医,公好食辛辣,膈有痰饮,但煎犀角、人参、腻粉、白矾,服之自愈」,李郎中如其言办,果然如此。之后「家人有疾,从其说皆验」,由此可见小莲精通医术。
而且小莲「言人休咎无不验」,可见她也精通卜算之术。
小莲精通卜算、医术,显然亦属术狐,这是唐代术狐观念的延续。但亦因此,「精于法术」这一特点并没有使狐妖群体中化出一种独特的新形象,其从一开始便是作为狐妖的其中一个特征存在,所以笔者姑且称之为「术狐特征」。
关于古人对狐妖能知休咎这一特殊能力的认识,大概是来自汉代或更古老的民俗文化认识。
在中国古代的占卜民俗中,根据不同的动植物、器物,甚至鬼怪的鸣叫声占测吉凶祸福是占卜的一种重要方法,如釜鸣占、鸟鸣占、狐鸣占等即是这类占卜法。
所谓狐鸣占,就是依据狐狸的鸣叫声占测凶难,此外还有相应的厌禳之法以祛邪禳灾。
狐鸣占的文献在传世文献中难觅其迹。2009年新公布的日本杏雨书屋藏一件编号为羽044的敦煌文书中所保存的狐鸣占相关内容是目前所见唯一传世且较为完整的狐鸣占文献。
透过解读该文献的内容,可知古代中国曾有通过狐鸣占测凶难的卜算文化和与之相应的厌禳方法。现实中的流行民俗文化,是这份狐鸣占文献得以被记录下来的前提,所以这份文献产生的时间就应在以狐鸣预凶为狐信仰重要内容的汉魏南北朝时期。
历史上,狐鸣占产生的最早时间已无从可考,汉代之前,似乎也有这种民俗观念,这从秦末陈胜吴广借山中狐鸣威众以起义之事中可见。此例中的狐鸣,除了有威众之效外,也有被认为是预兆着秦朝的崩溃。
不过笔者觉得在此事中借狐鸣的既然是陈吴二人,那么从秦朝的角度去解读这声狐鸣似乎不太自然。所以此例也未必与狐鸣占有关。
但起码在汉代,这种占验法就已经很普遍了。古籍中也能找到不少与狐鸣相关的记载,大多都明示狐鸣为凶兆。
《焦氏易林》卷十二载:「狐嘈向城,三旦悲鸣,邑主大惊。」
同上书卷十六载:「鸟飞狐鸣,国乱不宁。下强上弱,为阴所刑。」
《论衡》卷十六《遭虎篇》载:「古今凶验,非唯虎也,野物皆然。……卢奴令田光与公孙弘等谋反,其且觉时,狐鸣光舍屋上,光心恶之。其后事觉,坐诛。」
《隋书》卷二二《五行志上》载:「(梁武帝)中大同中,每夜狐鳴闕下,數年乃止。京房《易飛候》曰:「野獸群鳴,邑中且空虛。」俄而國亂,丹陽死喪略盡。」
在唐代及五代时期,世人仍以狐鸣为不吉之兆,狐鸣占仍在当时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得到应用。而敦煌文书羽044之《狐鸣占》的面世说明在宋代早期,狐鸣占及其相关记载至少仍在敦煌地区流传并存在着。
虽然往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狐鸣占作为一种杂卜法逐渐被人们遗弃,最终走向了消亡。但或许便是因为狐鸣占在古代民俗观念中还残留着一些烙印,所以古人在塑造狐妖形象的时候也相信它们具有预知和避祸的能力。
或是呼应这种狐妖法术化的现象,且又因术当出自书,所以唐代小说中出现了一个新概念——「狐书」。
所谓「狐书」,亦称「天书」,是狐学习修炼法术的秘籍。狐妖幻化人形须借法术,作祟惑人,与道士术士斗法亦须有神术法力,千岁狐要想通天,更应掌握高超法术。总之,狐种种作祟护身之法,「预知休咎」,祸福于人之术,均得自「狐书」。
《太平广记》引有一则唐人小说,其中便有关于「狐书」的描写。
《太平廣記》卷四五四引《張簡棲》
南陽張簡棲,唐貞元末,於徐泗間以放鷹為事。……俄至夜,可一更,不覺至一古墟之中。忽有火燭之光,迫而前,乃一塚穴中光明耳。前覘之,見狐憑几,尋讀冊子。其旁有群鼠,益湯茶,送果栗,皆人拱手。簡棲怒呵之,狐驚走,收拾冊子,入深黑穴中藏。簡棲以鷹竿挑得一冊子,乃歸。至四更,宅外聞人叫索冊子聲,出覓即無所見。至明,皆失所在。自此夜夜來索不已。簡棲深以為異,因攜冊子入郭,欲以示人。往去郭可三四里,忽逢一知己,相揖,問所往。簡棲乃取冊子,話狐狀,前人亦驚笑,接得冊子,便鞭馬疾去。廻顧簡棲曰:「謝以冊子相還。」簡棲逐之轉急,其人變為狐。馬變為麞。不可及。廻車入郭。訪此宅知己,元在不出,方知狐來奪之。其冊子裝束,一如人者,紙墨亦同,皆狐書,不可識。簡棲猶錄得頭邊三數行,以示人。今列於後。(下缺)
张简栖所获「狐书」之册,文字虽不可识,但可兼照其他故事中关于狐书的描写来进行推测。
唐·張薦《靈怪集·王生》寫杭州王生在圃田見二野狐倚樹人立,「手執一黃紙文書」,王生奪得,「才一兩紙,文字類梵書而莫究識」。後野孤化王生弟而來,詐回狐書,並說「今日還我天書」。
狐妖称「黄纸文书」为「天书」,兼照《张简栖》所言,天书所载乃狐书(狐的文字),与「梵书」类似,看了也不懂。
《廣異記·孫甑生》中寫孫甑生放鷹入一窟,「見狐數十枚讀書,有一老狐當中坐,迭以傳授」。
故事中孙甑生夺书而还,翌日便群孤上门,持金赎书。孙抄写一本,狐授口诀传法,孙便成为术士。以上很清晰地说明了狐书乃道术之书,所载的道家法术可使凡人成为术士。
不过狐书内容也不止这些。
《宣室志》卷八《林景玄》寫,墓穴中狐翁「手執一軸書」,其書「點畫甚異,有似梵書而非梵字,用素缣為幅,僅數十尺」。
从狐翁「吾命属土也,克土者木,日次于乙,辰居卯,二木俱王,吾其死乎」之语来看,这册狐书当是五行占卜之书。
《河東記·李自良》寫家中道士「執兩紙文書」,「其字皆古篆,人莫之識」,狐道士稱之為「天符」。
这册狐书当属符法之书。因为道士是天狐,他的符法大约也得自天上,故称「天符」。前引《灵怪集·王生》中王生所夺文书,狐亦称为「天书」,大概亦出自天宫。
《廣異記·韋明府》的天狐崔參軍「懷出一文字」送給丈母娘,令其模仿著寫,以治作祟的狐小妹,並言「天曹知此事,我幾死」。
此处的「文字」显然也是自天上来的秘卷,所以天狐崔参军才会说,要是被天曹发现祂私相授受,祂就危险了。
另外还有一些例子,大概都是符法书。
《廣異記·李萇》中狐妖送給李萇的書帖「符法甚備」。
《稽神錄·張謹》中狐妖說「此符法我之書也」。
狐书中还有一种「通天经」。
《類說》卷一一《玄怪錄·狐誦通天經》
裴仲元家郭北,因逐兔入大冢,有狐憑棺讀書。仲元搏之不中,取書以歸,字不可認識。忽有胡秀才請見,曰行周,乃憑棺讀書者。裴曰:「何書也?」曰:「通天經,非人間所習。」
此经名《通天》,而且「非人间所习」,显见是狐修行通天术的秘籍,也正是所谓天书、天符之类,大概是狐书中最宝贵者。
有的狐书不是符禁占卜之书,但也为狐所珍秘。
《乾𦠆子·何讓之》中,何讓之在墓窟所得「一帖文書」,「紙盡灰色,文字則不可曉解」,乃是天狐「應天狐超異科策第八道」。
此亦即天狐的试帖,天狐凭此策登科,才能成为天帝近侍,故而视为至宝,不容他人 夺走不还。
狐书是出现在唐代狐妖传说中的新内容,具有浓重的道教意味,也是道教文化渗透影响狐文化的结果。狐书正是道书,但又因唐代存在以狐指胡的文化现象,所以其上所载的文字又类似梵文。
狐书是狐的看家法宝,犹如命根,绝对丢舍不得。特别是「天书」、「天符」和「通天经」这些,由于是得自天宫,所以便更不能泄露于人世。
《廣異記·韋明府》中,天狐崔參軍就因為洩露了天書,被天曹幾乎打死,並遭受流放「長流沙碛」。
《廣異記·孫甑生》中,道士孫甑生得狐所傳授秘訣,狐叮囑他「不得示人」,若違犯必定死於非命,也是同樣原因。
因此,狐妖失去狐书后,便要百计夺还,于是有种种赎书、索书、骗书之事。
明·冯梦龙《醒世恒言》第六卷《小水湾天狐诒书》结末四句诗有云:「狐有天书狐自珍。」这是很妥帖的断语。
狐书之说,后世小说仍有描写,大多循唐代旧说,别无新意。
北宋·劉斧《青瑣高議》別集卷一《西池春遊》云:「有耕者耕壞冢,見老狐憑腐棺而觀書,耕者擊之而奪其書,字皆不可識。經日復失之,不知其何書。」
南宋·陸游,其詩亦用狐書典,《劍南詩稿》卷六七《林間書意》之二:「不讀狐書真僻學,未登鬼篆且閒遊。」
又卷七一《閒中偶詠》之一:「不識狐書那是博,尚分鶴料敢言高。」
清代狐妖之「学狐特征」及「术狐特征」的残余体现
在后世的妖精故事中,作者不管赋予妖精多么完备的人性,总要多少显示其异于人类的特性。
除了因化形不完美所遗留的破绽之外,故事中的狐妖之异于常人处多体现在其具有的特殊能力,而这些特殊能力大都可以归纳为「术狐特征」。
在后世文人的笔下,术狐特征虽然比学狐形象被更为广泛地描写,但后者在诸类狐妖中也算是经久不衰,直到清朝仍能看见它们的身影。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四《雨錢》載:「濱州一秀才讀書齋中,有款門者,啟視則一老翁,形貌甚古。延入,通姓氏,翁自言:『養真,姓胡,實狐仙。慕君高雅,願共晨夕。』生故曠達,亦不為怪。相與評駁今古,殊博洽,鏤花雕繪,粲於牙齒,時抽經義,則名理湛深,出人意外。生驚服,留之甚久。」
此处之「胡翁」毫无疑问亦是「学狐」,不过相比起它在唐代的那些死于非命的前辈们,胡翁可谓是真正的觅得知音。
由于狐妖修炼仙道,所以清人认为狐妖擅医。这种擅长医道的狐妖,不仅有高超医术,且讲究医德,常能救死扶伤。其身上体现了唐代狐妖的博学特质和清代狐妖的善性。
《聊齋誌異》卷五《上仙》云:「南郭梁氏家有狐仙,善長桑之術」。
这「长桑之术」即为医术,相传春秋良医扁鹊之师名长桑君。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二《狐知医》也写到狐仙能医,记有许多事迹。
结语
古人认为狐是「智兽」,由此便生出狐妖喜读书的传闻。这种书生化、博学化的狐妖形象亦因此诞生。总览中国妖怪传说,唯独狐的才智得到突出强调,并体现在学问之上,其他妖物莫能相比。
如果说狐妖的淫媚化所反映的是古人对狐的恶意,那么狐妖的博学化所反映的,该是六朝学士对狐的好感,对其智慧的赞美。说不定学狐就是士人用以自我投射到志怪小说中而创造的形象角色。
唐代学狐出现了博学化和法术化的现象,狐妖除了精通经史,竟也变得多才多艺起来,甚至还通晓各种法术。这种情况对后世狐妖观念影响很大,几乎所有狐妖故事里的狐妖或多或少都会体现这种特征。
此外,晋唐两代的学狐术狐故事,对日本的狐妖传说也造成了颇大的影响。吉野裕子《神秘的狐狸》中曾言……
日本《提醒紀談》中有白髮學狐,名曰幸庵及蛻庵。前者「常以佛理教諭他人」,「知吉凶禍福及將來之事」,後者「善卜筮」。
日本《其昔談》中也有「嗟來狐」,會讀書寫字。
其中的狐妖都有「术狐」及「学狐」的特征。
参考材料
《中国狐文化》P.66-67,74-77,123-126,李剑国
《一见罕见的「狐鸣占」文献及相关问题》王祥伟
文章来源于互联网:-《知妖》:狐文化特辑【十一】狐妖余论: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学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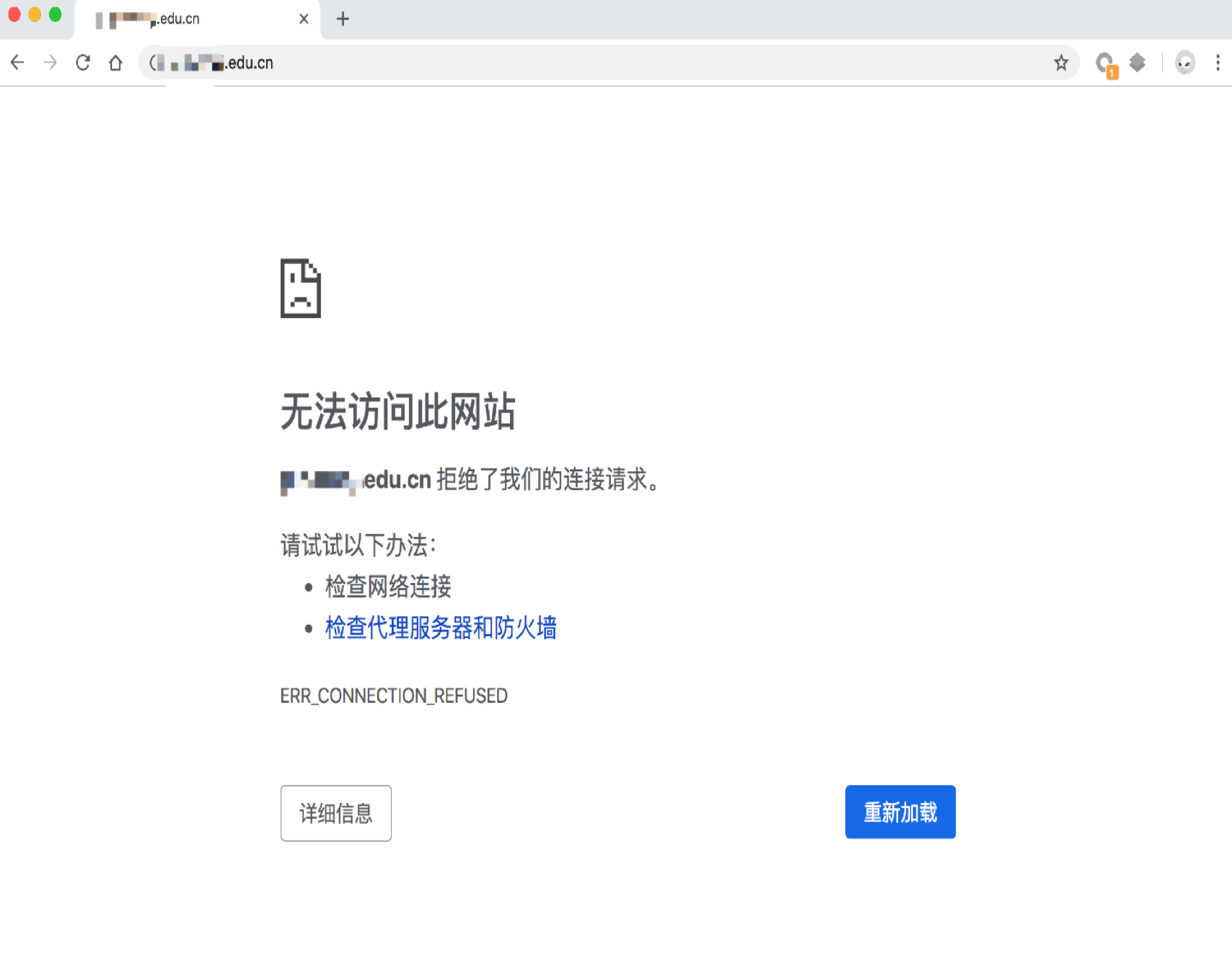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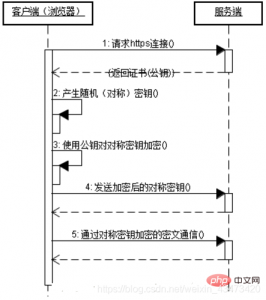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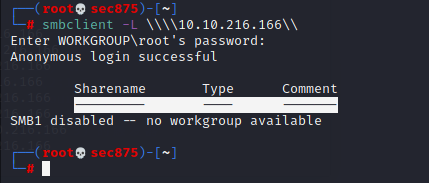



请登录后发表评论
注册